
唯色:满城回响救护车催命般的鸣笛声…… ——献给我的母亲,献给我们的拉萨
预先设好的手机铃响,提醒供酥[1]的时间到了,
我放下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2],
起身走向门口,将糌粑和特殊药粉搅拌的酥,
均匀地撒在熏黑的不锈钢盘子上,
打开电炉,烤出的香味随烟飘散[3]。
已值正午,烈日当空,白云寥落,
点开噶玛巴念诵《极乐净土愿文》的视频,
却听见不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
很急促,催命般,又时断时续,像是不只一辆,
像是满载了不少病人,需要快快地送走。
送往哪里?听说拉萨的方舱已增至八、九个[4],
而方舱这个词没译成藏语,若汉语发音不准,
就成了藏语谐音的猪圈或乞丐的房子[5]。
这些日子,这三十多天被“静默管控”的日子,
救护车的嘶鸣是这座空空荡荡的城市
唯一的最强音(想起新话“时代最强音”),
还有什么声音呢?啜泣,呼告,谁听得见?
院子的四面墙头有雀鸟啁啾,盛开的
月季红得像鲜血,被小蜜蜂无声地吸吮;
长得像花豹的野猫跃下堆满朽木的房顶兀自离去。
越盖越高的世俗居所遮挡了颇章布达拉,
也遮蔽了原本可以随风传来的风铃声。
我静下心,举起金刚铃,朝着香烟袅袅的
酥,摇响三次,并须念诵三次:嗡啊吽
多么盼望走了整整一个月的阿妈会听见,会再来……
然后,我会沿着那个永别的深夜,我消瘦的阿妈
被年轻力壮的天葬师放上担架前,给她穿上
她喜爱的那套绿衬衣、绿条邦典[6]的藏装,
从刹那空寂却残留香味的卧室抬出的路线:
穿过用一条条挽结的白哈达隔出的通道,
两边是残花凋落的纷乱枝条出自她的栽种;
绕过供着美丽佛陀塑像和大桶清水的木桌,
桌下用糌粑画了古老的雍仲符号,而窗户上
映出几十盏点燃的酥油灯,摇曳着,如同照亮莫测的中阴;
依顺时针方向转一圈,再依逆时针方向转一圈,
这是让亡灵找不到回家之路的意思吗?
不料,紧攥着拴在担架上的哈达走在前面的我
一个踉跄,是阿妈不愿离去吗?泪水奔涌,
走出大门……不,我不能走出大门,据说奥密克戎
仿如可怕的巨兽,张开血盆大口,蹲伏门外!
是的,我们都不能走出大门,所有人;
我们都要乖乖地听话,所有人;
我们都须随时听令,所有人(新话称“不漏一人”)
或者排长队做核酸,或者等大白[7]入户做核酸,
有天半夜还做过什么抗原,就像某种被操控的游戏,
人们啊,要活着还真是花样百出,心存侥幸,
最多隐约地感觉到有些深渊早在暗夜挖好,
对了,我们还要双手接过恩赐的连花清瘟[8],
我们还要感激涕零,三呼万岁……
但我此刻不关心疫情,我已深陷生离死别的疫情!
啊,我的阿妈,你走过的这条离开我的,
离开你多年前一手盖起来的这座宅院的路线并不长,
如今我每日三次供酥都会反复地走来走去,
会边走边念六字真言,声音很大,如同呼喊,
就仿佛,被打动的观世音菩萨会垂怜丧母的人……
而我抬头,深邃、碧蓝的天空一缕白云飘来,
于是我再也、什么都听不见:救护车的不停
哀号,金刚铃的三声脆响,法王声若洪钟的救度,
以及这些日日夜夜我的祈祷……我啊我
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那个生养我的亲人
最后的叹息:“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
2022年9月12日写,15日改,于拉萨
注释:
[1]酥:གསུར་是一种烟供。传统上,须用特殊药粉及“三白三甜”(酥油、牛奶、酸奶;冰糖、红糖、蜂蜜)与糌粑搅拌,点燃后或烤出的香烟是某种食物,以求上供下施,以及亲人亡灵享用。
[2]《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1939-2018)写的长篇自传体小说。
[3]传统上,是在陶罐内放置点燃的牛粪,再撒上酥,以供亡灵七七四十九天享用。
[4]修改这首诗时得知在拉萨盖好的、或临时设的方舱不止八、九个,而是二十多个,甚至更多,并扩延至附近的墨竹工卡县等。另外,将核酸检测为阳性、甚至也有阴性的人们拉往方舱的车,除了救护车,更多的是公交车,因为常常是深夜拉人,被拉萨人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戏称为“恐怖片:拉萨午夜的公交车”。
[5]藏语的猪圈发音“帕仓”,乞丐的房子发音“邦仓”,与汉语方舱谐音。
[6]邦典:པང་གདན།,藏人妇女藏装裙袍上的围裙。
[7]大白:也是中国发明的一种新话,指参与疫情防控的人员,因穿白色防护服被称为“大白”。
[8]连花清瘟:中国发明的用中药材制成的以对付新冠病毒的药,是中国卫健委的推荐用药。
来自: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920202213113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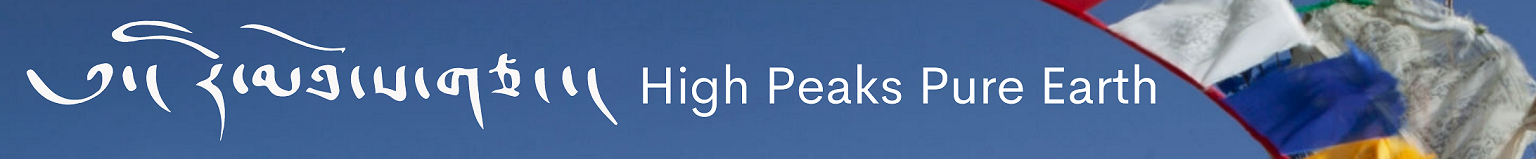



Follow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