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感慨磕长头的虔诚灵魂时,
可曾想过他们身下的公路是谁修的?
电影《冈仁波齐》近期引起热议,由于我的西藏背景,每每有类似的文艺作品上市,总会朋友主动与我交流观影体会。但我最近忙于钻研川普大帝和国企党建,没看过《岗仁波齐》,自然也不会有体会。不过,我看了电影的海报,倒是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不论是在文艺作品,还是现实的藏区旅行中,我们都能看到,长头都是在公路上磕的。那么,公路是谁建的?
是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由一代代的建设者建的,这包括最初的十八军和西北野战军进藏部队的战士、包括建设时期的工程兵和各族工人,还包括今天来自西藏本地的以及四川、陕西、河南多地的民工、挖掘机、搅拌机和卡车个体经营户和各类小型包工头。
相比之下,公路的建设者们,无论是工程师、包工头还是民工,都不如朝圣队伍那么有艺术气息。我敬重磕长头的人,能有毅力花很长时间做一件事的人都值得净重。但我并不太关注这些,我更敬重的是建设者百折不挠的奋斗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大精神。
虽然肤浅或深邃的文艺青年喜欢将现代化和传统对立起来,诟病西藏的发展让西藏不再纯洁,但事实上,朝圣之路并非来自传统,而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产物。具体来说:
第一,在旧西藏,是不存在全程磕长头到拉萨朝圣这种形式的。因为过去没有公路,西藏复杂、险峻的地形,很多地方猴子四条腿过去都不容易,人磕头就更做不到了。
第二,朝圣之路是存在的,但这在旧西藏是只有极少数贵族或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他们能做到,不等于普通藏族能做到。
当然,我提出上述观点时,也常常遭到朋友反驳,包括藏族、汉族以及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各外国民族。他们大多也都能列举些各式各样的证据,从历史上的朝圣书籍等有一定根据的资料到“上次我在西藏玩的时候人家跟我说”等道听途说的段子。
所以,我也想认真谈谈这个问题,从历史资料和自然规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普遍的朝圣之路在旧西藏不可行?
- 人身依附与物资匮乏
朝圣首先要有人身自由,但是旧西藏实行的是庄园农奴制,农奴擅自离开庄园视作逃亡,换言之,占人口比例95%的农奴是不具有自己决定自己是否能去朝圣的权利的。并且,即使得到庄园主批准,绝大多数农奴也没有可以支撑朝圣的物质基础。
具体来说,第一,旧西藏庄园制实行的是乌拉差役制度,乌拉差役具有劳役地租特征,它要求租种土地的农奴家庭必须派出一个或以上壮年男性劳动力全年在农奴主的庄园服役,相应的,农奴家庭拥有一定的份地,但这份份地就需要其他人来耕种,这意味着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两个成年男性才能维持生计。因此,“不能分家”的现实需求孕育了“兄弟共妻”的婚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在庄园劳动的农奴肯定不能获得朝圣的许可,而他在份地劳动的兄弟如果去朝圣了,全家老小都有饿死的危险。责任感决定了,一个男人不会丢下自己的家人,仅仅为了个人的灵魂的升华而去朝圣的。
第二,根本没有足够的物资。1951年,西藏人均粮食占有量是135公斤,历史时期的粮食产量数据也不可能比这高多少,尚大幅低于比人均200公斤的温饱标准。
而历史上的朝圣之路,最近的山南、日喀则核心区到拉萨也要走三个月到半年(路途远,交通差,另外,做不到磕长头,也至少要做到逢庙必拜,不然怎么是朝圣,这也会耗费大量时间)。不算其他开销,一个人至少需要100公斤口粮(长途跋涉消耗大),农奴家庭从哪里积攒这些粮食?
另一方面,现在朝圣者普遍必需较多的酥油、奶渣等脂肪补给,否则撑不过残酷的气候。而在旧西藏,普通农奴基本吃不到酥油的,在1990年代以前,西藏农村的流行民谚是“小孩子不能吃酥油,吃了会掉耳朵”,吃酥油习惯的真正普及,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产物。
- 后勤补给的困难
在今天物资丰裕的情况下,朝圣也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专门的后勤团队。在今天比较好的道路和补给以及商品流通(有钱可以买到东西)条件下,后勤团队也藏族朝圣者队伍中是标配。
一般来说,现在的朝圣者中,老人、妇女或者年纪较大的男子居多,一般是几个人组团朝圣,因为这样比较节省后勤力量。过去,后勤团队使用平板车居多,那么至少要有两个成年男子才能保证平板车的持续运作。
朝圣是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建后勤团队,比如等自己的儿子挣了一些钱、有空闲的时间,或者通过半是人情半是非货币补偿方式找同村好友。这些年,汽车在藏区越来越普及,后勤人力下降,一个成年男子当司机也就够了。
然而,不论是汽车还是平板车都是在公路上才能走的,西藏到处都是高山,和内地的平原环境不一样,过去平板车不具备长距离通行能力,就得需要大牲口(牦牛或犏牛),而在旧西藏90%以上的农奴没有大牲口。而且就算有大牲口,牦牛的问题是,到了河谷地区,它热的受不了,老想下河洗澡;犏牛的问题是,到了高山地区,它冷的受不了。
没有补给,怎么支撑朝圣之路?
- 随处化缘可行吗?
当然,也有朋友反驳我说,朝圣之路不需要补给,朝圣者可以随处化缘。现在,很多书籍里也这么写(主要是现代用汉语写作的书籍)。
藏族同胞待人热情确实值得称赞。即使在旧西藏,物资十分匮乏,如果有人去敲门化缘,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拿出自己不多的粮食。但化缘的前提是得先见到人,而在朝圣之路上,绝大多数时间不可能见到可以化缘的村庄。
具体来说,长期徒步旅行,长期锻炼的强壮男性在平原地区的平均速度一般是50公里/天,而在高海拔和崎岖山路双重效应叠加下,一天最多走10~20公里(这个众多徒步驴友都验证过),过去没有公路,行径速度要更低,也就10公里,如果是磕长头的话,一天能走5公里就不错了,朋友们不信可以自己实验下。
这样,问题就来了,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核心区之外,50公里见不到村庄依然非常普遍,骑友们经常要靠90~110公里一个的道班以及公安检查站休整。那么,旧西藏的朝圣者们去哪里化缘?
在没有公路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迷路问题我们就不说了。
- 恐怖并漫长的冬季
以上还不是最多的困难,朝圣中最难的是:除了拉萨市辖区以及日喀则和山南的核心区,其他地区来拉萨朝圣肯定要超过半年,四川、青海藏区要超过1年,那就不可避免的遇上长达半年以上的冬季。
西藏的冬季,在拉萨等城市的城区其实不难过,由于日照强,基本无降水,以拉萨为例,冬季白天的气温一般能有十几度度,比北京、上海舒服多了。夜晚的温度就会骤然下降,当然大家都是在屋里睡觉,也没事。
但朝圣就不一样了,在旧西藏,绝大多数实践肯定要露宿野外,那么如何抵御零下1、20度的严寒?而且,上面说的是最好的情况,是在3000多米海拔的河谷地区,但是,在朝圣之路上,绝大多数都是4、5000米的高山地区,这些地方,7月都能下大雪,冬天夜晚的温度一般在零下3、40度。在冬天,如何保证自己不冻死?
而且,山区一下大雪,积雪经常就是在半米以上。现在,工程兵在西藏冬季也要随时待命,用大型机械也要挖个两三天才能勉强恢复公路通行(参见今年初的西藏雪灾,央视报了救灾情况)。在旧西藏,既没公路,又没工程兵和挖掘机,在高山地区碰上雪灾,就是死。而大雪是每年的常态。
前两天,有藏族学生和我说,藏族谚语“有水即可饮茶,有草即可住下”。这话是对的,但有水有草在西藏可不是容易的事,别看西藏到处是草原。在长达半年的冬季,既没水(只有冰,变成水得有燃料,可是燃料在哪里呢?),也没草。
现在我们在观察西藏时(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视角),过于强调西藏、藏族和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下意识的认为“藏族只追求灵魂的纯净,不希望更好的物质生活”(也就是说,“物质决定意识”在西藏是不成立),然而,事实上,没有现代化和国家建设带来的交通设施、增产增收等等,现在我们在西藏常常能见到的、被视为藏族“纯净灵魂”象征的磕长头去拉萨朝圣行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曾经在公路上碰到过一位磕长头的藏族老阿妈和陪伴她的家人,她们邀请我吃他们自己做的奶渣。闲聊中(我会一点藏语,也有人帮助翻译),我问老阿妈:“磕头的时候都为谁祈福?”她说:“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也为辛苦修建这些公路的大好人祈福”。
我很好奇,“为什么要为修路的人祈福?”
老阿妈说(她儿子在一旁补充,语句是我整理过的):
我们家在的地方,山高谷深,地域辽阔,交通非常不方便。以前没有路,村里人一辈子别说去拉萨朝圣,连县城都未必去过。生了病,就只能用土办法治治,请人念经,熬着。要是没有这些路,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有机会去拉萨朝圣?
一路上,我看了那么多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拜了那么多寺庙,我给自己积下了功德。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修了这些路的大好人、大恩人,不管是藏人、汉人,他们真是做了大善事,积了大功德,佛祖一定会保佑他们的。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物质丰裕、现代化和虔诚信仰对立起来。然而,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和现代化才提供了真正可供实践的信仰自由。
可能没读过多少书的老阿妈倒是比很多读过很多书的人明白的多。
影像的表达和商品化:关于藏地题材电影的一些思考
首先必须坦白,我从不阅读影评。这篇文章也不是对于电影《冈仁波齐》的评论,我更无意贬损作为本片导演的张扬。只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这部电影和它所引发的讨论促使我分享自己参与电影制作的经历和想法。
我是一名正在攻读西藏历史和文学的学生,从2015年起我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一些涉藏影片的制作。因此我的立场自然地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基于我自身对于现有理论尚不成熟的理解。
1
我第一次观看《冈仁波齐》是2015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当时正值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有天晚上我怀着期待走进了影院观看这部影片,却失望而归。这部电影在西方收获了一些赞扬,有评论家称赞导演选用素人演员,电影本身耐心的叙事节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广角取景也被许多人所称道。但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并不突出,不久后回归学业的我便全然忘记了这回事。
在如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形势下,我们正面临着图像的泛滥。当我们传播厚重围裙背后虔诚的朝圣者在雪地中勇往直前的图像时,我们正在消费和再生产关于藏地和藏人特定的描绘。
如今的西藏已然变成“信念”,“信仰”,“纯净之地”的象征。而这样的描绘实际上是将主体从其自身日常的情境中移除,使他们变成了盛放外界观众和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焦虑、恐惧、欲望和想象的容器。
我并无意质疑藏人对信仰的赤诚之心,也无意否定藏地的壮丽景观。只是影片的叙事——符号和意味之间的那一层关系,虽然看起来平实自然,却植根于一个更深层的文化关联体系。除去对导演身份的考量,不受约束的影像表达可能会危及,甚至消灭外界认知者和主体间发展互动关系的正常过程。
对于这些看似良善的图像日益增长的传播和消费,让我们逐渐相信那些兜售给我们的神话,从而徒增困惑。随着藏传佛教在国内和西方前所未有的兴盛,藏地和藏人都成为了资产阶级想象的客体——即映射他们自己所憧憬事物的对象。
2
关于西藏的抽象化表达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而且这一历史与西方殖民主义和人类学、民族志的诞生相辅相成。其后,电影和大众媒体又成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在当代的语境中,尤其对于独立的电影制作而言,关于西藏的描绘一直深陷在对现状不满的资产阶级生出的渴求与想象中。
在这一部分的文章中,我将阐述电影《冈仁波齐》是如何被漫长历史中的特定描绘所摧残,而我们对于认知自身主体性的抗拒又是如何使我们在诸多创造性领域——包括当代艺术、电影和文学中捉襟见肘。
我将着眼《冈仁波切》的核心内容,但无意在此一一指出它叙事中的缺失。这部电影构建在一个极为简单的公路叙事之上:朝圣者心中的信念和信仰帮助他们克服了去往拉萨的路途中自然环境的种种艰险,旅途中的死亡与新生命的降生更是完成了一个格外陈词滥调的关于“轮回”的叙述。
虽然距离我观看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故事的细节与我的论点并无太大关联。在电影里,朝圣这一行为——表现在转山,磕长头,及种种其他仪式上,实际上已经从日常鲜活的情境中位移,来用于填补当代中国的某种缺失。关于仪式及其实践的图像,从而成为了可以被娱乐性地围观的事物,而不再被视为一个族群生活的一部分来理解。
更进一步说,对于“虔诚”图像的消费,实际上填补着这个社会日益缺失的,甚至被剥夺的东西。我并不是研究电影的学者,但是我将张扬1999年的作品《洗澡》视作他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做的一次冥想。在《洗澡》中,普通人的生活在商业化所构建的新型空间中得到转换。澡堂象征着一种熟知,一种永恒,一种集体。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曾有数部影片讲述这种根源及传统的错位。而“澡堂”已垮,西藏正沦为这些艺术家们的“香格里拉”。
电影中天葬的场景让我回想起来到西藏的西方早期人类学家为了他们所谓“文明化”的使命,极力寻求记录异域、“蛮荒”的事物。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现如今对于藏传佛教的描绘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种欣赏,而我认为,他们与那些民族志先行者们所共享的其实正是对于普世意义的强调,却省略掉了产生这些文化的特定社会条件,并且将外界的观者塑造成了主体。西藏变成了超越时间和历史的存在——一副治疗我们现代社会世俗问题的灵丹妙药。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颇具预言性地写道:这世上存在的所有事物终将归为一张照片(everything in the world exists to end up in a photography)。图像正逐渐与经验划等号,而经验又逐渐被视作与知识和能力等同。因此,将影像描绘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非常成问题的。张扬的电影模糊了纪录片和剧情片的边界,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是作为电影人必须至少尝试去寻求表现这个主体与认可其在影像叙述史上的争议和复杂性之间的平衡。而我们,身处被动旁观者的角色中,则正成为商品化自身文化的共谋者。
3
我绝不认为只有藏人才能拍摄关于西藏的影片。相反,我很高兴如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在拍摄制作关于西藏的电影。我更无意暗示我们已经沦为关于自身描绘的囚徒。随着越来越多的藏人开始学习和制作电影,我相信我们正处于西藏电影领域发展的关键时期。出于对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崇敬之情,我才在此与各位分享了我的一些想法。
如今主流语境中的电影人有一类似乎在反刍早已令人厌倦的关于西藏的刻板描绘,而另一类则退避至对于自己故乡的民族志式的纪录中。不消说后者的确是一种值得认可的努力,但是我想要鼓励年轻电影人们更多地去突破边界进行思考——我们不应永远停留在“学习电影,回到故乡,拍摄关于当地寺院的作品”这样的局限里。
似乎现如今藏地新电影的“宣言”由书写藏语剧本,启用素人演员和藏人技术团队所构成。但是,究竟什么是“藏地电影”呢?
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电影会在无意中强调我们一直以来寻求逃避的叙述方式。本土(故乡)总是与“古老”,“纯净”和“未被玷污”这样的表述联系起来。而许多人却没有意识到“本土”和“过去”实际上建构于它们自身内部,同时被自身所建构。面对许多僵化的思维模式,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把被理所当然视为“常规”的东西问题化,复杂化,甚至肢解。
其实我并不想在电影中寻找真理或者现实。我认为那样的电影实际上背叛了艺术家应有的清高。我自己对于电影的理解一定会被他人认为是激进而发散的,但我仍然希望能看见更多的藏人导演在风格,主题,甚至声音上做出不同的尝试,以期有一天我们能够庆祝更多在独特题材之外获得的成功。
http://mp.weixin.qq.com/s/i7FAXCWbQKLD32mYba2VW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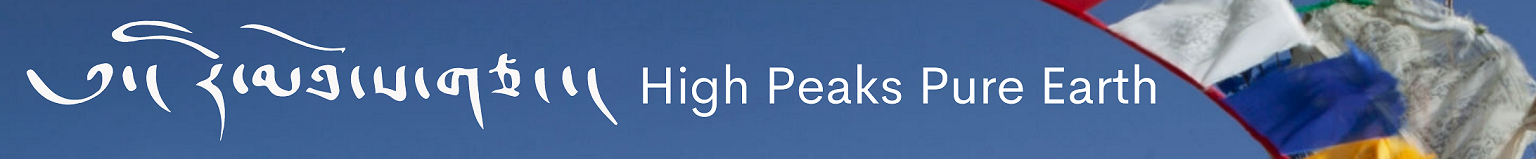





Follow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