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第一次看见汉人,可能是1952年。那是准备修路的汉人,拿着旗帜,吹着口哨,带着各种仪器。大人们都叫他们是“加米色波”,意思是黄汉人,因为他们穿的是黄颜色的军装。那之前就听说过汉人了,说汉人要吃小孩,是魔鬼。所以汉人来了,村里的孩子们又害怕又激动,胆战心惊地偷偷跑去看。通司(翻译)是个藏人,抓住一个男孩子问了句什么,男孩子吓得结结巴巴地,胡说了一通,让汉人们哈哈大笑。孩子们吃惊地交头接耳说:快看快看,汉人的笑和我们的笑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村现在是乌郁乡的扎西岗村,当时属于我们康嘎家,康嘎是我父亲原来家族的名号,我父亲分家后另立的名号叫哲江,我就出生在乌郁康嘎家里,那是1943年。扎西岗下面有一块荒地,长不出青稞,全是石头、砂子,后来“农业学大寨”时使劲地翻过,也长不出青稞。当时筑路队的帐篷就搭在那儿,四四方方的,很多很多,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一辈子要住在那儿。
筑路队可能是1953年来的,起先来的都是汉人,后来招了一些当地的藏人。公路是从拉萨修到日喀则的,但不是现在的新公路。当年修的那条老公路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用了,但有时也可以用一用。在村子附近过去还有一个兵站,现在废弃了。
筑路队的汉人都穿的是蓝衣服,所以都叫他们是“加米翁波”,意思是蓝汉人。那时候,我们哲江家开始盖新房子,后来成了乌郁乡的乡政府,现在已经被拆了。我爸爸是努玛溪卡的溪本(庄园主),经常会被筑路队请去吃饭。可能因为我长得好看吧,父母总是带着我一起去赴宴。我就是在那样的场合第一次吃到了油炸花生米,觉得香极了,一个劲地吃个没完,筑路队的本波(官员)就把装花生米的碗放到我的面前,我很高兴,把胸前的藏装往下一拉,花生米全倒进了怀中,结果回家后,胸前一片油。那时候我刚满10岁。
筑路队的汉人常常来我们家里,跟着他们的翻译都是藏人。我姐姐就爱上了一个翻译,名叫贡保才旦,安多藏人。他戴着鸭舌帽,穿着中山装,个子高高的。他第一次来我家,我姐姐就被迷住了。可是父母已经把她许配给了日喀则城里的一个贵族少爷,那个少爷不好看,黑黑的,鼻子很大,跟着他父亲来过我家里,我假装倒茶看清楚了他,赶紧跑去给不能露面的姐姐一形容,姐姐根本就不想嫁他了。
筑路队的炊事员喜欢我们家的青稞酒,我就经常带着佣人去送青稞酒。我那时正是好奇心很强的年纪,喜欢看稀奇,于是看见他们吃白米饭,菜就是黑豌豆,远不如我家里吃的好。炊事员常常回赠我们一缸子四川豆瓣,跟印度辣椒的味道不一样,很好吃。缸子是白的,上面写着红色的汉字,后来我跟你父亲谈恋爱后,见到他也有那样一个缸子。
筑路队在我的家乡差不多呆了一年多,有指挥部、医院,还搭了演戏台,篮球场。筑路队有时候放电影,我第一次看电影时眼睛都直了,但是放的什么电影我忘记了,反正一句汉话也听不懂。宣传队经常来演出,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鹅毛扇子跳舞,我稀罕极了,回家后用羊毛做成扇子,学她们跳舞。
1953年,我哥哥从拉萨回来了。他很小就被送到拉萨,在纳戎夏医生的私塾学校上学。我哥哥比我大6岁,那时候已经很革命了,家里二三十个佣人吃饭时他就坐在中间,说要把土地和牛羊分给他们,佣人们全都埋着头偷偷地笑,他们一定觉得哲江家的少爷疯了。我父母很生气,训斥哥哥说,如果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的话,不会留下一块干的石头;可是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你在这儿瞎说什么?
那时候,我哥哥已经把他的长发剪成了革命式样的短发。他拿着剪刀,到处剪头发。剪佣人的辫子,还剪了我的辫子,我不愿意,可是哥哥一剪刀下去,我只好哭着认命了。我害羞死了,家里人都叫我“加姆果”,意思是汉女人的头,我只好整天在头上裹着个头巾。
剪了头发的第二天,家里来了筑路队的汉人要买糌粑,那个最大的本波挂着相机,看见我就要给我拍照片,是在我家房顶上拍的,我穿着平时的衣服,靠着拉登(日喀则话,拉萨话叫“拉足”,过新年时在房顶插经幡的地方),后来妈妈看见照片不高兴,说我什么地方靠着不好,非要靠着拉登。
那个拍照片的本波,一只眼睛没有了。他从来都戴着墨镜,镜片黑黑的,看不见他的眼睛。村里的孩子们都很想看见他取了墨镜的样子,有一次果然看见了,那只瞎了的眼睛里装了一个像玻璃球的东西,很吓人。想起来,那时候见到的汉人里面最像魔鬼的可能就是他吧,所以他要给我拍照,我不敢不答应,但照相的时候连一点笑容也没有。
那次一起来的翻译不是姐姐喜欢的那个安多,是打折多(康定)的一个藏人,叫白洛,后来当过区交通厅的厅长,现在退休了,有时候会在打麻将的场合碰见他。几天后,他把洗了的照片送过来了,还洗了好几张。
不久,我被哥哥带到拉萨去上学。我们住在舅舅家里,就在木如寺那边,我舅舅当过帕里宗的宗本(县长),解放军进藏的时候,他是昌都总管阿沛的侍卫官,昌都战役后,他也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我被送到刚刚成立的拉萨小学,可是我太想家了,在得到了一套呢子做的汉装后,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可是哥哥坚决不同意,硬是让我学了快一学期,正巧我爸爸到拉萨办事,我就跟着父亲一块儿回家了,把那套汉装送给了佣人的儿子。
在家里的快乐日子没过多久,哥哥又回来了,然后又把我带到拉萨,继续在拉萨小学学习。哥哥越来越革命,加入了当时风靡拉萨的青年联谊会,那是一个很时髦的组织,像个演出团体,很多年轻的贵族男女都在里面搞活动,但我还小,对那些没有兴趣,我只想回家。1955年,哥哥去了北京,读中央民族学院。他一走,我也就骑着马回到了乌郁乡下。
1956年,我爸爸被人毒死了。第二年,我和姐姐去了拉萨,从此许多年之后才回过乌郁。姐姐是为了逃婚,而我是不喜欢新来的继父。我们俩在拉萨上了藏干校,就是培养藏族干部的学校,算是就此参加了革命。
图为我少女时节的母亲(摄影者:我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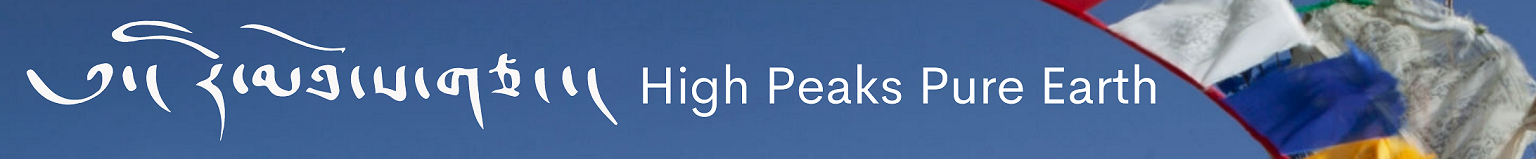



Follow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