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尧西达孜的蜘蛛》
那天下午阳光猛烈
照耀在一张张平凡的脸上
脸是金色的,如被点石成金,变得异常宝贵
走过江苏路。是的,拉萨南面的江苏路
这违和感十足的命名,本不属于这里,你懂的
我比他俩年长,是个头矮小的阿佳[1]
我们说藏语。兼说汉语和英语,但我只会汉语和藏语
身后有人尾随。几个人?
就像甩不掉的尾巴,拐角处的獐头鼠目
被吞噬了小心肝的可怜虫
路边树荫下,散坐着开店的外地人,脸上无光
所谈论的,与生意有关,便添了几分焦躁
走过北京中路,这座圣城早已嵌满类似命名
就像一个个占领,谁都不足为奇,习以为常
阳光啊金色的阳光,将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地面的花砖上
将挂在高处的、各处的摄像头,投射在我们的身上、
所有人的身上……似乎脊背发凉,但管他呢
我不愿回头张望,或停止不前
大步走着,咧嘴笑着,我们都很帅
珍惜这貌似自由的时刻,争相叹道:“好幸福!”
径直右拐:这是第几回看见尧西达孜[2]?
依尊者家族冠名的府邸,六十多年前建成,一半已成废墟
不过我不想复述历史:最初的欢聚,迅速降至的无常
包括被迫弃之,饮泣而走,被外人霸占:穿绿衣的、
穿蓝衣的,各色人等乃饿鬼投胎,寄居蟹的化身
如今,旧时的林苑,成了停车场、川菜馆、大商场
主楼与外院多处坍塌,几乎没有完好的窗户
有一次,我们站在商场顶层,居高临下
惊讶于它像无法愈合的伤疤
惊讶于它原来离颇章布达拉[3],这么近,这么近
含泪自责:无能为力的废物啊
步入空旷的外院:一半杂草、野花
一半停放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
一对像是打工者的男女提着塑料袋擦身而过
四五头漆黑而高大的獒犬,锁在楼下的角落
仅能露出锋利的牙齿、绝望的眼神,仅能发出无用的狂吠
它们属于附近开饭馆的四川老板,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
数日后再次潜入,碰到他来喂食
摆出主人架势,但虚张声势的驱逐并未生效
就叫来穿保安制服的男子,是藏人
我便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令他无措,呐呐不成句
从遍地垃圾的底层上楼
屏息穿过裂缝交错的回廊
几排当年购自印度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
连串的花纹与阳光下的倒影构成虚实不明的异域迷宫
凭栏环视,原本的白墙斑驳,黑色的窗框开裂
雕绘了神兽、祥云与莲花的檐头,竭力支撑着架构房屋的朽木
而在十几根柱子依次排列的阴暗大厅,乱扔着几件劣质桌椅
应是被最后的搬迁者废弃。几束光线
自一排天窗斜射而入,尘埃飞舞,幻影幢幢
如昔日头戴面具的僧侣缓缓跳起羌姆[4]
我注意到靠近西北面的窗户,由缺口如刀刃的玻璃
恰好望见颇章布达拉,似乎也能望见,忧虑中有担当的尊贵青年
一转身,却被柱子上悬挂的一面残破镜子所惊
那里面,有一个无依无靠的自己,带着渴望隐遁的神情
我不敢靠近,怕瞥见1959年深夜一个个仓惶离去的身影
怕听见已在异国度过许多岁月的尊者低语:
“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5]
会不会,我的前世恰在此处生息,经受了所有诀别?
会不会,曾经痛不欲生,却又为苟活费尽心机?
陡然升起逃离的愿望,但仍徘徊于布满某种痕迹的房间:
有的墙上贴着旧日当红的香港明星头像
二十多年前的《西藏日报》有中共十四大的消息
一幅临摹布达拉宫的印刷品破烂不堪
有的门上贴着中文写的“福”和“新年大发”
长髯飘飘的中国门神右手持宝塔左手举铁锤
有的门已重换,用红漆刷了两个很大的中文:“办 公”
有的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
某个角落,一具骷髅状的羊头有一对空洞无物的眼眶
一对烧焦的羊角弯曲伸延着,像是曾经拼命呼救
某个角落,原本用阿嘎[6]夯打的地面不复存在
却从泥土的地表长出一株小草,居然生机勃勃
另一处,扔着巴掌大的木块,应从往昔华丽的柱头脱落而坠
彩绘犹存,雕刻亦在,像老屋的缩影,我悄悄地放入背包
以系在胸前的一粒绿松石[7]为隐秘的指引
最终我命定般地遇见了它:特嗡母[8]!
高悬在一扇倾颓的窗户外那危险的半空中飘荡着
受困于自己吐丝织成却几乎看不见的网上飘荡着
它已成一具干尸,如临深渊:这一片的塌陷尤其惨烈
它是这里唯一死亡的生命吗?
它是这里唯一存在的守护者吗?
它不自量力的布局,是想捕捉不邀而至的恶魔吗?
它像另一面镜子,垂挂在我的眼前,逆光中骨骸漆黑
以某种挣扎的形状,变成一个隐喻,我不敢触碰,怕它瞬时消失
想当年,在此相伴共生的动物一定不只它一种
一定有猫,也有老鼠
一定有狗,那是拉萨特有的阿布索[9],主人的宠物
在佛堂、客厅和睡房跑来跑去或安然入眠
而大狗,我指的是从牧场带来的獒犬,与看门人呆在一起
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忠心耿耿,不容侵犯……
特嗡母,这是蜘蛛的藏语发音,“母”为轻声,几近于无
特嗡母哒,这是蜘蛛网的藏语发音,“母”仍细微,如被吞咽
虽比其他众生的生命力更顽强,更容易藏身他处而幸存
但也更容易孤独无告地死于非命
毕生编织着“天生就像一座监禁宿敌的城堡”[10]之世间网
却被自缚,难以自拔,恰似我们啊我们莫测的命运……
2017-7-31至9-19,北京
注释:
[1]阿佳:ཨ་ཅག藏语,姐姐。
[2]尧西达孜:ཡབ་གཞིས་སྟག་འཚེར།藏语,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之名。依传统也是房名。尊者家族从安多迁至拉萨之后盖的府邸,也冠此名,位于拉萨城中心,距离布达拉宫很近。
[3]颇章布达拉:ཕོ་བྲང་པོ་ཏཱ་ལ།藏语,布达拉宫。
[4]羌姆:འཆམ།藏语,金刚法舞,由僧侣演示。
[5]这句话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第75页,尊者达赖喇嘛语,约翰.F.艾夫唐著,台湾慧炬出版社出版。
[6]阿嘎:ཨར་དཀར།藏语,白色物质。藏地特有的一种建筑材料,风化的石灰岩或沙粘质岩类被捣成的粉未,一般用于建筑物的房顶及地面。施工时,将其掺水砸实、磨光,建成后平整、光滑、坚实,不渗水,有如水泥。有民歌:“阿嘎不是石头,阿噶不是泥土,阿嘎是深山里的莲花大地的精华。 ”
[7]绿松石:གཡུ།藏语,在藏地民间又称“魂石”,曲杰·南喀诺布先生写道:“根据藏族传统,灵魂可指一个依处或被拟人化为一件东西,如一块宝石、一座山、一个湖泊等。”绿松石即“一块充任具誓神灵‘依处’的魂石。”出处见注释10。
[8]特嗡母:སྡོམ།藏语,蜘蛛。蜘蛛网,སྡོམ་གྱི་དྲ་བ།།藏语,特嗡母哒。
[9]阿布索:ལྷ་ས་ཨབ་སོབ།藏语,Lhasa Apso,拉萨狮子犬。
[10]这句话引自《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第19页。曲杰·南喀诺布著,向红茄、才让太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来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8/blog-post_3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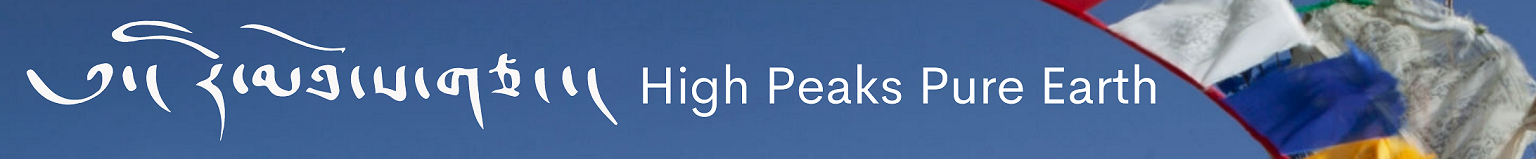




Follow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