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我对遍及图伯特大地的废墟怀有深深的兴趣,我对散落在拉萨城里的废墟怀有深深的兴趣。废墟几无例外,皆是当代历史中的政治暴力造成。而我对废墟的兴趣何以体现?除了书写,就是摄影。如果我会绘画或音乐,那么画笔、乐符或歌声,也将是废墟的证据。是的,证据,或者说见证。多年来,我其实更多用文字和相机记录的,逐渐集中于这两座废墟:喜德林废墟和尧西达孜废墟,前者的前生是一座寺院或者说经学院,后者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

关于废墟的书写,散见于我用中文写作的十多本书籍。除了书写,我很想通过我的“废墟摄影”,来显现被占据、被遮蔽、被隐形的拉萨历史与拉萨地理。犹如城中之城,人中之人,以及死亡中的死亡。废墟中各种各样的细节非常多,我更留意的是,比如,尧西达孜空旷的庭院里怒放的花朵、主楼塌陷处悬挂着风干的蜘蛛、墙上残留的《西藏日报》或中国明星画像、往昔佛堂柱子上悬挂的破碎镜子,以及内院的某个房间,当年用阿嘎土夯打得比今日的瓷砖还结实的地面不复存在,却从泥土的地表上长出一株绿色的植物。我似乎也由此多少领悟到那难以名状的意义。
而我的废墟摄影并非出自一个专业摄影师。所以我随心所欲,使用了各种器材拍摄,如胶片相机、数码相机(单反数码及普通数码)、Gopro甚至手机。用Gopro和手机拍摄简直过足了瘾,一次就能拍数千张。这些海量的图片,似乎是构成了这两处废墟的图像志,多少具有了文献的价值,算是对拉萨老城中一个行将消失的特定区域的记录,我这么自认为。有时候,我也会自拍,或者以喜德林废墟里残缺的壁画为背景,或者面对尧西达孜废墟里残破的镜子若有所思,那镜中人,似我又不似我,却更似过去岁月中住在这里的某人。这种疏离却又亲密的感觉,还真刻骨铭心。
如果你注意到每天深夜,我在几个社交网站上发布磕一百零八个等身长头(其实早已超出了这个数)及祈祷嘉瓦仁波切千诺(尊者达赖喇嘛了知)的消息,并附上这两处废墟的照片长达一年多,大概可知,事实上,我在这两处废墟看到的林林总总都是具有意义的。每一个局部,每一处阴影,其实都是拉萨的密码,图伯特的密码。正如被翻译为名叫《照片的历史》(The Photograph)这本书,就一位通过照片保护旧巴黎的摄影师有这样两句评论:“(他)把巴黎看做一个博物馆——照片保留了历史,成为某些特别的、魔法般的地方的护身符,成为城市意义的一部分”;“他要留下历史的证据,通过图像的力量来保护失落的都市景象的氛围和完整”。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做到这样。

两处废墟所不同的是,喜德林废墟是半开放的(但今年已被禁足),其周遭是数十户各种人家居住,因此总是看得到各种人的各种日常生活:操持太阳灶的主妇在烧水或熬肉汤,干木匠活的男子正又锯又刨,年轻女子将一盆盆鲜花抬到阳光下,或将晾晒好的棉被拿回家,而五六个中年男女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有一次,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尼坐在台阶上摇着转经筒,就跟她聊了一会儿,得知她本在山洞闭关修行,却被军警赶出,不知还有没有重返的一天。经常能遇到在这里租房住的汉人和回民,有一个满口黄牙的汉人已六十多岁,他满腹牢骚,深深地不爱此地,却又不愿回老家,他的余生会在哪里度过?而尧西达孜废墟早被禁足多年,虽然也遇见过在里面停放自行车或摩托车的汉人民工,遇见过在外院楼下圈养藏獒的汉人老板,似乎唯独他们拥有自由出入的特权。
想要补充的是,我在两处废墟都见过动物。喜德林废墟的狗和猫都各具特色,个性十足。其中一只黑狗,模样狡诈,却格外胆小。我欺负它,用自拍杆追逐它拍,它又气又怕,在废墟前的太阳灶之间穿梭躲避,直到看我追不上(其实是我不想追拍了),它才露出狰狞样子,尖声狂吠,我被它逗得笑出了声。而在尧西达孜废墟,有被圈养却凶狠的藏獒,四五头,漆黑而巨大,禁闭在外院二层楼的楼下,仅能露出锋利的牙齿和绝望的眼神,它们属于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看我们在拍照,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除此,我在尧西达孜废墟发现的生命,准确地说,已经死亡的生命,是一只挂在自己吐丝而织就的蛛网上的蜘蛛干尸,悬在内院主楼倾颓的房间外那危险的半空中飘荡着。它仿佛是这里唯一的主人,守护着废墟也就守护着过去。我只能把镜头靠近它拍摄。之后形成的图像里,它与周遭的残破房屋构成了仿佛意义深远的画面,我只能意会。然而当年,在这大屋里的动物一定不只蜘蛛一种。一定会有猫,也有老鼠;一定会有狗,那是拉萨特有的阿布索,主人的宠物,可以进入佛堂和客厅、睡房;而大狗,我指的是獒犬,会与看门人呆在一起,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忠心耿耿。显然,蜘蛛比狗和猫的生存力都更顽强,也更容易藏身,更容易活下来,最终孤独地死去,高挂在几乎看不见的蜘蛛网上,恰似我们莫测的命运。

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喜德林废墟废墟里的壁画。我最初见到是2003年,从左到右,由前至后,残缺不全的断壁上残留着一片片画面,若非亲眼目睹,都不敢相信这里会藏着如此惊世的美。虽因自然风霜和人为磨损使得画面有剥落,有裂痕,但立体的肌理感仍未磨平,纯正的色彩感仍未消褪,这与传统的矿物颜料有关。仔細地看,诸佛菩萨的微笑依然莞尔,诸佛菩萨的手印依然奥妙,而护法镇伏的魔鬼依然怒目圆睁……是的,左边一层角落有一小片壁画让我迷恋,就像是我的秘而不宣的私人收藏,之后每次再去,我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探望,生怕消失不见。为此有一次小心翼翼地潜入废墟,站在壁画跟前用数码相机各种自拍,就像是将自己融入其中,再也不怕会失去。经堂后边那旧日佛殿有一面断墙全是佛陀托钵坐像,整齐排列,安静入定,却发现在其中一尊画像的眉心间,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洞,就像是子弹头穿过的痕迹,但后来再去,断墙倒塌的部分,恰有那尊中弹的佛像,实在可惜。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大雪中的喜德林卻是另一种面貌。废墟的残败和颓势并未被白雪掩盖,反而更加凄凉、肃杀。跑过来让我拍照的几个孩子,脸上有冻伤,流着清鼻涕,表情也僵硬。旁边拴着的一头黑藏獒,脖子上挂着染红的羊毛编的项圈,冷得簌簌发抖。这一切让人想起讲述伊斯坦堡前生今世的帕慕克(Orhan Pamuk)所说的:“下雪天的伊斯坦堡像个边远的村落,但寻思我们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与我们辉煌的过去靠得更近。”
然而有关喜德林废墟的最新消息,在2016年的第九天传来。当日,设在拉萨的《西藏商报》称:“喜德林寺要维修了,将以博物馆形式开放”。其中写道:“设计方陈先生介绍,这次喜德林寺维修的主体建筑是大殿,而大殿正好是整个喜德林寺受损最严重的部分,也是设计最难的部分。……设计维修首先参照了上世纪50年代的的历史照片,还有现场勘察的喜德林寺遗迹。……维修后的喜德林寺,将以博物馆的形式向大众开放。”

我于是想起多年前,第五世热振仁波切给当局递交允许他修复喜德林的报告,却被拒绝。还想起一个听说有着特殊背景却又有香港身份的北京摄影师,一直在建议当局将喜德林废墟改造成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展览馆。与此同步的是,2012年设在香港的《亚洲周刊》,第三十五期发表文章《汉藏不能忘却的爱国情》,作者是该杂志资深记者纪硕鸣,以党报的笔法改写了第五世热振仁波切的历史,把他的死亡说成是“因为坚守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正常关系,而被当时的分裂分子秘密毒死……”;更荒唐的是,比如这一段犹如“红色经典”影视神剧的情节:“亲英分子质问热振活佛:‘西藏何以要亲中国?’热振大义凛然地回答:‘一九零四年英国军队荣赫鹏攻入拉萨,军事赔款概由中央政府所付,所以如果不是中国的钱,岂能赎回西藏的身?’”而对喜德林寺何以成了废墟,则说成是“热振活佛死后,达扎先派人将他的遗体移至喜德林寺中,后又策划暴徒掠烧了喜德林寺。”
这篇文章还处处引述一位神通广大的“涉藏摄影家”的话,称这位热心的神秘人物要拍摄“热振活佛殉国故事”的纪录片和电视连续剧,并打算修复希德废墟,在里面展示所谓的“民族团结”的文献文物。这其实就是要把喜德林废墟改造为一个红色景点,向各方游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五世热振活佛惨遭英帝国主义分子与藏独分子的毒手之后,他的寺院被藏独分子毁为废墟,如今在致力于汉藏团结、祖国统一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下,重又恢复了原貌。
这是多么罔顾事实的后续啊。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光,将这么多年来在喜德林废墟拍摄的几千张照片默默地重看了一遍。与根敦群培一样,第五世热振仁波切也将被塑造成“爱国志士”隆重推出,没有比这些更无视真相的造假了。但我知道,我的喜德林废墟的摄影,算是对拉萨老城中一个行将消失的特定区域的记录,我还知道,我还会为即将华丽变身的废墟继续写传,还会为到目前为止尚不知下场如何的尧西达孜废墟继续写传,因为一位名叫嘎代才让的图伯特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废墟带霜,一道神授的光芒/从天空垂降。”是的,看见了吗?在因果轮回的光芒照射之下,一次次反复被捣毁的图伯特废墟,已成为永恒。
2016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来自: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9/blog-post_3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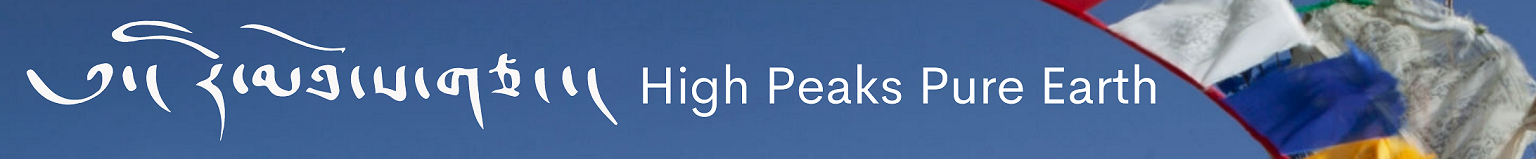


Follow Us!